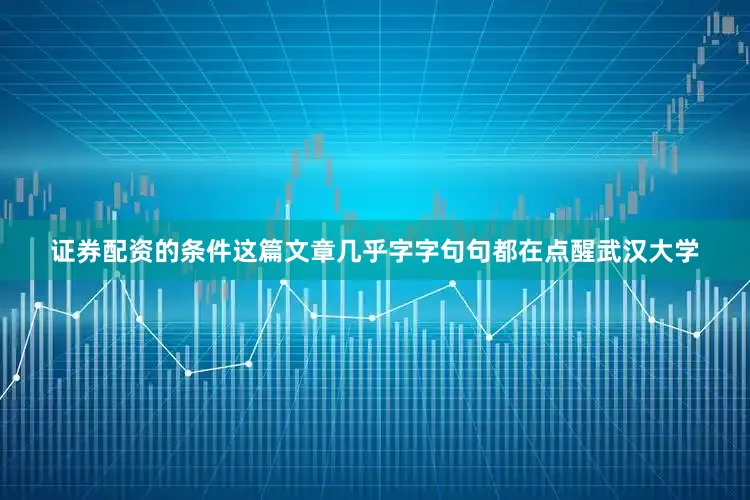在新中国开国元勋的夫人们中,彭真的妻子张洁清无疑是最独特的一位。
这位出生于河北的大家闺秀,自幼生活优越,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她最喜欢缠着自己的姑姑张秀岩,静静听她讲述五四运动中激昂的先进思想。渐渐地,张洁清的心中萌发了对共产党革命事业的深厚向往。
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求学期间,满腔热血的张洁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革命道路。她先后加入了“新兴剧社”、“师大生活社”等一系列进步团体,还积极参与北平妇女救国会的活动。1936年,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正式投身革命工作。
嫁给彭真之后,张洁清放下了自己的革命抱负,在那个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中,默默无闻地全心支持着丈夫的革命事业。
展开剩余91%丈夫彭真去世九年后的2015年春天,已经103岁的张洁清躺在病床上,临终时嘴角露出一抹温暖的笑容,对身边的儿女说:“我要去陪你们的爸爸了。”
随后,她在家人的哭泣声中,静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没有鲜花环绕,没有戒指光彩,张洁清为何甘愿成为彭真身边的绿叶,陪伴了他整整58年?这段革命爱情的背后,又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?
张洁清的姑姑张秀岩,是李大钊的学生,早年便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,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思想的熏陶,是一名积极投身革命的早期共产党员。
从小,张洁清和几个弟妹就在姑姑的熏陶下成长,家中十几口人纷纷投入革命事业,而张洁清则是最早踏上革命道路的那一个。
1934年,张洁清自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,暂居在姑姑家,随后赴天津培才学校任教。
从此,张秀岩以张洁清的语文教师身份做掩护,安排她一边教书,一边往返于北平和天津之间,秘密传递党的情报和宣传材料。
1936年秋天,张洁清接到姑姑的指令,下课后便赶乘火车赴北平。
当时上火车时都要接受女警察的严格搜查,张洁清每次左手拎着普通的皮箱,右手抱着一本教科书。
女警察总是把她的箱子翻得乱七八糟,张洁清巧妙地将许多漂亮衣服放在箱子上层,成功吸引了警察的注意,令他们没有发现藏在箱底的秘密情报。
一下火车,她便扮作一名来京探亲的外地人,步伐从容地走进北平西城区丰盛胡同的一处大院。
这处被前后两座大院包围的平房群中,有一处写着“大义社”的建筑,那里是许多社会名流常聚集的社交场所。
她怀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走进热闹非凡的“大义社”,迅速根据姑姑的描述,锁定了一个穿着大灰袍、身材高瘦但精神矍铄的男人。
这位男人原名傅懋恭,后改名为彭真。
那时,他刚从国民党监狱释放,暂居大义社,担任北平地下党的情报员,化名“魏先生”。
“魏先生”敏锐地察觉到这位二十出头、文静的小姑娘时不时偷偷观察自己,隐隐感到她身份不同凡响。
经过几次紧张而刺激的秘密接头,张洁清与彭真开始建立了工作联系。
随着她频繁穿梭于北平与天津之间,秘密传递党的机密文件与口信,她渐渐发现“魏先生”是一位沉稳可靠的领导干部,办事谨慎细致,常常为她的人身安全着想,对她关怀备至,令她把他视为亲切且令人敬重的大哥。
然而,两人的交往时间并不长,这段短暂的同事缘分很快告一段落。
几年后,张洁清再次遇见彭真时,已经是1939年。
那时,她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,根据中央指示,来到晋察冀根据地投身革命工作。
这位在大城市中成长的姑娘,初来乍到灰尘弥漫的黄土高原,对农村工作毫无经验,急切希望掌握技能,便申请进入党校学习。
在晋察冀党校上课时,张洁清万万没想到会与曾经多次传递秘密情报的“魏先生”重逢。
这位站在讲台上,温文尔雅讲授党的理论知识的“魏先生”,正是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兼晋察冀分局书记、党校校长的彭真同志。
张洁清认出了这位“魏先生”,彭真也认出了那个勇敢坚强的年轻姑娘,彼此重逢感到十分惊喜。
此时的张洁清已不再稚嫩,亭亭玉立,心中也悄然生出少女的情愫。
几年前秘密传情报时,她已从姑姑口中听闻“魏先生”的卓越才华与坚强意志,暗自对他心怀仰慕。
他乡重逢,张洁清对这位“魏先生”倍感亲切,因他年长自己十岁,身为党校老师,她既尊敬又不敢轻易靠近。
一天傍晚,下课后,彭真突然约她单独见面。
张洁清心跳加速,彭真也紧张得心脏狂跳。他回想起同事们的鼓励,凝视着眼前这位才貌出众的姑娘,深吸一口气说:“张洁清同志,我敬佩你的聪慧和才华,喜欢你的活泼和善良,你愿意和我谈恋爱吗?”
那一瞬间,张洁清脸颊绯红,仿佛置身云端。早已心动的“魏先生”终于向她表白,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恋爱不久后,那个冬天,张洁清的疟疾加重,连续高烧不退,身体虚弱得无法起床。
彭真发现她未到课,急忙到党校宿舍探望。
打开房门,见她面色苍白裹在被窝里,气息微弱,心疼不已,连忙走过去抓住她的手腕说:“不如到分局去治病,搬到我那里,让我照顾你吧。”
张洁清虽病重,却听明白这话中的深意,感受到彭真想与她携手一生的心意,含泪点头同意。
党校同志对视一眼,找来担架,将张洁清抬到彭真分局的窑洞中。
贺龙、吕正操、黄敬、关向应一旁欢呼“促成促成”,彭真和张洁清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结为夫妻。
有人问彭真为何喜欢上张洁清,他笑着望着妻子说:“我们是在地下工作中相识,战争年代谈恋爱,在艰苦的环境下结婚的。”
结婚后,张洁清与彭真相伴半个多世纪,共同度过患难与共的时光。
作为领导夫人,她从未有丝毫优越感,反而以彭真夫人的身份鞭策自己更加努力。
那时,张洁清被安排在晋察冀中央局机关秘书处工作,认真完成本职,同时协助丈夫整理文件、抄写材料。
彭真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递交的许多重要汇报材料中,都凝结着张洁清的心血与智慧。
战争年代,危险时刻时常发生。
1940年,敌军再度发起扫荡,县里老幼妇孺既组织反扫荡,又转移阵地。张洁清怀孕将近十个月,不得不跟随同志转移。
彭真当时在延安,浑然不知险情。
炮火连天,张洁清逃到盂县后,突然临产,只能躲进一座破败的教堂。
教堂窗户无纸封闭,寒风呼啸,她在这恶劣环境中生下第一个孩子。
刚生完,她用大衣裹住婴儿,继续上路。
身体虚弱又赶路,她实在走不动,倒在雪地中,同志们只得用简易担架抬她。
为了减轻同志负担,张洁清扔掉了大棉被,却因连翻四座山头被风寒袭击,落下终生难愈的病痛。
这种艰苦在她生活中屡见不鲜,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,她伴随彭真辗转各地,躲避枪林弹雨,忍饥挨饿。
曾经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,张洁清从未在任何时刻诉苦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彭真任北京市委书记,以她的资历与能力,张洁清完全有资格担任更重要职务。
但她选择了北京市委机关秘书的职位,甘愿做彭真身后的支持者,助力丈夫顺利开展工作。
她的几位共产党员妹妹认为她性格开朗,善于联系群众,又是大学毕业,理应独立成长,担任更重任,纷纷劝她改变。
张洁清却坚决摇头说:“你们别劝我了。”
事实上,彭真非常依赖她。
他有个习惯,讲话不看稿子,脑海中默写,然后对张洁清反复讲述,请她提出修改意见。
张洁清总能指出需要优化的地方,二人反复推敲,彭真因此上台无需稿件。
虽不带稿演讲,张洁清在台下仍认真记下简化内容,形成书面记录。
彭真担任重要领导期间,张洁清坚持写工作日记,详细记录彭真每日工作、活动、身体状况及气候变化,这一习惯持续了十多年。
她跟随彭真吃过不少苦,最艰难时,两人挤在十平方米的小屋中度过无数难熬日子。
张洁清无怨无悔,始终如一地照顾丈夫,辅助其工作。
但她从不干涉彭真的公务,也不参与任何保密工作,始终保持适度距离。
张洁清的女儿回忆母亲,“铁石心肠”,不轻易发脾气,但要求严格。
在北大学习时,有一次同学高烧昏迷,打电话让张洁清去接,张洁清却说:“麻烦你们租出租车,让她自己回来。”
即便为彭真生了几个孩子,作为母亲,张洁清并未将孩子视为生活中心,而是把丈夫作为生活重心,将支持他的工作当作党的事业。
因此她拒绝担任更重要职务,坚持把照顾丈夫和支持革命工作作为自己无上的使命,视为忠诚于国家、奉献人民的体现。
1997年彭真病重住院时,他对儿女说:“你们的妈妈非常了不起,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。”
张洁清听后泪眼婆娑,紧握丈夫之手,心痛地表示,首先作为一名党员,为失去这位开国元勋感到无比悲伤。
彭真去世后,张洁清每天清洁摆放有丈夫画像的瓷盘,默默追忆过去的点点滴滴。
她与彭真的爱情极为深厚,既有夫妻间患难与共的真情,也蕴含家国大义下对领导人的革命忠诚。
发布于:天津市融信配资,德创配资,真正的实盘配资平台查询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